|
墨光都借性灵传
──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罗 应 涛
(宜宾学院 四川宜宾 644003) 摘要: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认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关键词:张问陶;性灵说;张扬个性;天才;灵感;独创精神
张问陶是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大诗人,我们今天对他的研究还十分不够,但他的同时代人对他推崇备至,评价很高。他的诗论虽无专著问世,却在其论诗诗和大量诗作中有充分体现。主要可见于《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赠徐寿徵诗》、《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题朱少仙同年诗后》、《题方铁船工部(元鵾)诗并呈吴谷人祭酒》、《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代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自题》、《自题诗草》、《和少仙(朱文治)》、《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以及《冬日游浣花草堂……》、《寄稚存》、《雨后与瞿生论诗……》等诗中。在以上各诗及散见于张问陶大量诗歌中的诗学观点,体现出张问陶诗学思想的诸多精辟见解,有一个相当完备、独具卓见的诗学理论体系。本文将对其性灵说作一初步探讨。
作为清代创作丰富的大诗人,张问陶接受了明清诗坛"性灵"说的影响,并且从自身之特点出发,又作了发展。他认为,诗歌作品的审美内涵在于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等的感性显现。他在其最早的《论文八首》中就说:"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性灵"诗论贯穿于张问陶整个一生的诗歌创作之中:"剩此手中诗数卷,墨光都借性灵传"(《秋日》)⑴"仗他才子玲珑笔,浓抹山川写性灵"(《题子靖长河修禊图》),"不斗性灵斗机巧,从此诗人贱于草"(《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留佛看古今,笼诗写性情"(《潼川夏日游琴泉寺……》),"语真关血性,笔陡见灵光"(《小雪日得寿门弟书》),"诗人骨死性情在,时发幽光夺明月"(《拜纳旃先生墓》),"传神难得性灵诗"(《梅花》),"性情图画性情诗"(《题武运听雨图王椒畦作》)。船山诗主"性灵"的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三十一岁时写的《论诗十二绝句》和四十九岁时写的《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中。在《论诗十二绝句》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子规声与杜鹃声,好鸟鸣春尚有情","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在《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绝句中,他又进一步重申:"诗人原是有情人","先天开一画","万化无非一味真"。张问陶认为:诗歌必须真实地反映诗人的个性、精神、真情、血性,正如孙桐生在《国朝全蜀诗抄》中概括的:"作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
" 性灵"是什么呢?性灵派首领袁枚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所写的《钱玙沙先生诗序》中有"既离性情,又乏灵机" 一语,可见出"性情"和"灵机"合言,就是"性灵"。性情,或"情",或"真情",指人的个性和感情;这主要是后天感染薰陶的结果,与人的处境、心境密切相关。"灵机",指人的天才和兴会,天才受之了天,即人的先天素质,是属于人的本色和自然;兴会,指触物起兴,是诗人在某种特殊情景下,主客观偶然遇合,各种信息骤然沟通,意象纷呈,文思泉涌的灵感到来时的状况。所谓兴,一般也说"灵机",或"灵感"。兴会产生主要在于机遇,在于造化,非单方面人力所能为之。情、性情、真情、气质、个性、欲望,这些都是每个人独具而与众不同的,既有高尚和卑俗之分,而不同的高尚和不同的卑俗之间又判然有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诗作只有从"我"出发,抒写诗人自身的个性、才情,才能发出"新声"。就是灵机,天才与兴会,还得立足于个性独异的个体之上。因此,张问陶论诗,既专主性灵,就必然看重诗人自我的作用,尤着重于张扬诗人的主体意识。
用诗来抒写自己的真情、本性,是张问陶一贯的诗歌主张,贯穿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之中。张问陶坚信,只要从自我性灵出发,写出自己的真阅历、真感受,诗便是绝对个性化,具有艺术独创性,谁也无法重复的。他在《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删诗》中说:"少作重翻只汗颜,此中我我却相关。"作者所珍重、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因为这些诗真实表达了他的思想感情。在《论文八首》中,张问陶说:"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认为诗无我之真情实感、真心实意,皆为无用之作。"我将用我法,独立绝推载。……悠悠三十年,自开一草昧……我面非子面,斯言殊可拜。安知峨眉齐,不出五岳外!"(《冬夜饮酒偶然作》)作诗力主用"我法"写"我面",坚持"著我"创新,陈腐的封建儒家诗教和规范可以不顾,其勇气和胆识令人佩服。"诗人作事何不可,直使古人来见我"(《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说明读古人作品,向古人学习,不是抄袭、模仿古人,而是要被我所化,为我所用。"秋斋孤咏心无慕,下笔非韩亦难杜"(题方铁船工部(元鵾 )诗兼呈吴谷人祭酒》)表明作者写诗,全从抒写一己之性灵出发,全然不依傍古人。张问陶认为,诗歌审美本质的显现和传达,是诗人"自我"情志向外释放的强烈要求。"热肠涌出性情诗"(《赠徐寿徵》),"使笔如心心如血,作诗犹是扬风烈"(《徐节母殷儒人诗为寿徵作》)。在张问陶看来,作诗是诗人感情难以自禁的抒发,只有从诗人自我内在"性灵"出发,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
诗中的"性灵"如何产生?张问陶认为来自三个方面: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结合。
第一,创作主体所固有的、独特鲜明的情性、个性或天性。这是决定创作成败的首要条件。这正如托尔斯泰所说:艺术家"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并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及言辞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⑵王夫之《姜斋诗话》说:"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主张诗中必有"自我",就是强调艺术表现要个性化,要有独创性。袁枚在《续诗品》中提出"著我"的主张,继承明代李贽、徐谓、汤显祖、公安三袁追求人的个性自由的观点,强调艺术表现要有个性化和独创性。张问陶主张写诗要出自诗人"性情"、"灵机"和"血性",即出自"自我"之"性灵"。从创作过程来考察,客观描写对象要诗人"自我" 去认识、感悟、体验,在诗人的人生经历中去获得。"诗情关岁序"(《秋怀》),"奇诗乱后多"(《冬日游浣花草堂……》),"燕南尘土江南月,尽向毫端滚滚来"(《题张莳塘诗卷时将归吴 县即以志别》),张问陶这些诗,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诗的情思和意象,来自诗人对描写对象的感知、提炼、整合和变形, 在诗人的支配和熔铸下进入诗作。张问陶认为,诗中之境,是诗人"自我"心境的写照,他说:"情真境岂伪"(《怀亥白兄寿门弟二首》),"诗中开悟境"(《黄小松作诗龛图寄法梧门祭酒为题一律》)。张问陶从创作实践中,深知风格是作家的"自我"精神个性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贯的创作个性。他说:"题诗无处能忘我"(《寄稚存》),"乱世雄心郁,才高逸气真"(《题花王阁剩稿》),"间气毓奇人,文彩居然霸……冷肠辟险境,灵心恣变化……才横雄剑飞,胆裂皇天咤……"(《读任华、李贺、卢仝、刘叉诸人诗》)。张问陶一再表明的是:诗人"自我",即独具的个性,性情,才情,天性,是决定艺术表现个性化和独创性的根本。黑格尔对创作主体"自我"与对象的关系,说得与张问陶类似:"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由创造者的主体性来的。"⑶他又说:"抒情诗的出发点就是诗人的内心和灵魂"。⑷"主体性"即由作者"自我"的个性、情性、才情、天性决定的。
第二,在创作主体的静观默照下,表现对象所显示出来的灵性,这是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审美发现与感悟,即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张问陶认为,创作要处于"闲肺俯""心空"的"天然"状态之下,即审美对象的自然造化与创作主体脱尽尘俗桎梏的超然物外的自在状态之下,创作主体于静观默照之中获得审美对象的"天趣"。然而,要得"天趣",须待"天机",即对象所蕴涵的天然内质与主体本质因偶然机遇而对象化的过程。"天然"因乎"天机",获得"天趣",从而产生诗的审美素质。"浮云过太空,无心忽相遇。人生随天机,即事有真趣。"(《六月二十八日偶遇亥白兄过东读书楼》)"浮云过天空,"即天然的自在状态下的审美对象。"无心忽相遇",指创作主体在超然物外的"心空"状态之下,与作为自然造化的客体偶然相遇,于是,创作主体即于对象中发现"自己的人生"。主体灵性在偶然机遇下,与对象的灵性相碰撞,物我交融中,直观感悟到宇宙人生真谛。张问陶在《江南诗意》中说:"物情也似人情好,谁领天机注我诗"。他认为,主体有"人情",客体有"物情",都处"天然"状态,二者不期而遇,交相融合,即有"天趣"。在"物情"、"人 情"这对矛盾中,人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主体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诗人须高扬主体意识,才能写出性灵诗歌。
第三,性灵是主客体交相融汇而产生的诗歌审美境界,既"天真",又有"天趣"。"缘情"是诗歌的审美本质。"人生随天机,即事有真趣。"(《江南诗意》)不仅要刻画描写出审美对象的"物情",审美对象的天然姿质、风神气韵,还要渲染、烘托出"人情"投射于"物情"之后,产生的天然的审美特征--"性灵"。"天籁自鸣天趣足",主体割断了尘俗侄梏的羁勒之后,与对象自然而然地交相融汇,形成"天趣"。"天籁"与"人籁"--名心退尽的超然之情相融,从而获得天趣,产生性灵之诗。
创作主体的"灵性",在诗歌创作中是起主导作用、根本作用的。人与人的"灵性"是不同的,同一个作者,由于人生阅历的丰啬,环境心境的改变,思想观念的转化,其"灵性"也是要变的。这个主体的变化,自然要影响对客体的认知、体验、感受、领悟。所以,张问陶认为只有从"我"出发去把握对象,创作才能独出心裁,独出新意,不依傍古人,以崭新的面貌展示于人。诗不依傍古人,要走创新之路,是否要向先贤圣哲学习,是否要向唐宋诸家学习呢?答案是肯定的。"土饭尘羹忽斩新,犹人字字不犹人。"(《题屠琴隖论诗图》)《韩非子·外储说上》:"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以食也。"以尘沙作羹,以泥土当饭,是儿童从其天然本真出发的一种游戏,一种创造。文学艺术创造亦当如此。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字字犹人",然而,又字字句句"不犹人"。船山先生还谈到对"雷同"的认识。如果发生"妙语雷同自不知"的情况,不仅不必忧,而且应以为喜 。这只能是"前贤应恨我生迟",这种情况也"胜他刻意求新巧"(《论诗十二绝句》)。在《重检记日诗稿自题绝句》中,船山对这种"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况,又进一步加以解释:"新奇无力斗诗豪,几度雷同韵始牢。香草美人三致意,苦心安敢望离骚。"说明雷同难以避免,并非有意与前贤争胜。
"空灵不是小聪明"(《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写诗不能光凭性灵,若只凭性灵就能写出好诗,那么,人人都有性灵,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张问陶认为:做出性灵诗,还要仰仗天才和灵感。张问陶在《题屠琴隖论诗图》之七中指出:"妃红俪白想千年,祸枣灾梨亦惘然;辛苦啖名皆劣伯,仙才何暇计流传"。
但是,"资质""禀赋"最初都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倾向,一种萌芽",它的成长、发展和实现决定于社会环境和其他种种条件,决定于人们持久不懈、专一而不傍骛的努力,决定于人们经久不衰、挚着虔诚的兴趣。张船山强调"仙才"(也就是"天才")包括的内涵似乎还要宽广,除了先天资质禀赋的优异外,还包括融有"天真"、"天然"、"天机"、"天趣"在内。船山诗云:"每从游戏得天真"(《论诗十二绝句》),"自磨碎墨写天真"(《题黄左田同年》)。"天真",作者发自于生命的本真,是不加掩饰的情性的自然流露,随性任之,绝无矫饰,是描写对象的气韵风神的自然表现,是创作主体主观领悟到的表现对象的客观审美本质,还有由此二者形成的诗歌内在艺术本质的美。"天然"是指表现对象的自然造化与创作主体脱尽尘俗侄梏超然物外的自在状态。"天机",指表现对象蕴涵的天然内质与主体本质在对象化过程中所显现的情性感悟。"天趣",包孕于诗境象中的天然之趣。"天真"、"天然"、"天机"、"天趣",都指创作中,无论主体、对象、艺术表现还是艺术作品本身,都要求做到本真状态,自在状态,超然感悟,随性渲泄。
是否如此自在、本真、随性、适情,就是天才?船山以为还要经过诗人艰苦奋斗,即"修"、"养"和"炼"。"修":"修心参内学,经世耻空言"(《中年》之二)。"养":"金石图书养性情"(《文泉教廉以诗送行赋此留别》),"君有烟霞养性灵"(《寄亥白兄兼怀彭十五》),"宽闲养性灵"(《六月三日送吴季达同年入盘山读书》)。"炼":"百炼功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这种"天才",既关乎"天真"、"天然"、"天趣"、"天机",是主体对客体的随性适性的感悟,必关乎造化,即自然和社会人生。客观现实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张问陶从自身的生活和创作实践出发,深黯此理。他说:"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用他的创作实践来说明:"老屋生前破,奇诗乱后多,无家寻弟妹,有泪哭干戈。沟壑谁收骨,乾坤许放歌。锦江空岁月,留滞恨如何。"(《冬日游浣花草堂……》),"燕南尘土江南月,尽向毫端滚滚来"(《题张莳塘诗卷将归吴县以志别》其二),"诗情关岁序,秋到忽纷来"(《秋怀》其一)。诗之情思、意象来自随情适性的人生体验和自然与社会的天供地献,有此,方得成"天才。"
船山还说:"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仙句偶成。(《论诗十二绝句》)"名心"即名利之心,"道心"即悟道之心。所谓"悟道", 是诗人以道喻诗,一方面,指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而参透人生哲理;另一方面,也指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而参透了诗艺的精髓。要"修"、"养"、"炼"出作诗"天才",必消除名利之心,使创作主体脱尽尘俗桎梏而超然物外。"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论诗十二绝句》之三),方能在作诗时让"天籁"自鸣,"天趣"自足,让诗意从性情中自然流露出来。总之,只要写出自我的真情,便是"天籁",自有"天趣",诗人便可成"天才"。而天才之作,不计流传而自流传千古不朽。
张问陶还认为:要写出性灵诗,必须有灵感。船山诗中多次论及灵感。他认为灵感到来时,天机启动,想象和联想发挥到极致,诗思泉涌,审美意象便破空而来,极具个体化的性灵诗便产生了。他说:"一片神光动魂魄"。"神光"即"灵光",就是灵感。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谈到灵感特点的是晋代陆机的《文赋》:"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张船山讲灵感之来是:"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论诗十二绝句》),"笔有灵光诗骤得"(《秋夜》),"心直与天谋"(《使事》),"一气如云自卷抒"(《论诗十二绝句》)。对这种形象思维中因偶然机遇的触发而产生的豁然贯通、文思泉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而写作格外得心应手的高效率创作状态,船山极有体验,因而也最能抓住其特征:它的产生是"忽来"、"骤得"、"聚如风雨"、"天上落将军",就是不期而来,不招而至,偶然突发;它出现后的精神状态亢奋紧张,专注迅捷,"跃跃诗情","诗魂欲上天","魂魄动",文思如潮,左右逢源,妙笔生花,魂惊魄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迷狂"状态,诗情奔涌而至,使创作主体入迷忘我;"散如烟","景过终难补旧诗",灵感来了如烟如雾,若不及时抓住,就无踪迹可寻。这种现象,苏轼比作抓"迷犯"一样火急:"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勒惠田二僧》)。性灵在灵感中自然产生,若妙手偶得,便在灵感中自然凝结为意境"空灵"的性灵诗了。
张问陶力主性灵,其旨归是实现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就必然要触及沈德潜等倡导的儒家封建文学思想和翁方纲的作诗规范。
清乾隆年代,继王士祯神韵说之后,主要由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和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说三家争胜。沈德潜坚持的理论根本说来是三点:一,诗关乎教化;二,诗必温柔敦厚;三,诗要合乎古之高格。翁方纲主张肌理,主张"无一字无来历","将诗当作考据作",如袁枚在《答李小鹤书》中所言:"近来诗教之坏,莫甚于以注疏夸高,以填砌矜博。据摭琐碎,死气满纸,一句七字必小注十余行,呤人舌举(举有口旁)口呿不敢下手。性情二字,几乎丧尽矣!"于是讥之曰:"天涯有客号呤痴,误把抄书当作诗。"(《续元遗山论诗》)性灵派与沈德潜格调说的分歧,是自然性情的自由抒发与封建儒家文学规范的分歧,属思想内容的范畴;而与翁方纲肌理说的分歧,是诗还是非诗的分歧,主要属于艺术的范畴。船山论诗诗中多次对沈、翁的主张进行了批判,《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之三:"模唐规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又如《论诗十二绝句》之十二"文章体制本天生,只有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又如《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诸君刻意学三唐,谱系分明墨数行。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船山认为苦苦坚持规唐模宋,即使写出几首诗来,也如残花败蕊一般,没有生气,没有光彩。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一生从事解经,为经籍作注:梁代太子萧统则选编两汉以来诗文为《文选》传世。他们都靠依傍前人而分别创立训诂学和文选学,为世效法,故曰"门户好"。今人愿为其奴婢,以儒家信条和宋代理学入诗,以考据训诂入诗,虽曰"门户好",但恐难以标当代之新,立当代之异。船山诗矛头直指沈、翁诗论,用语激进尖刻,也是一种纯任性情的表现。他强调作诗无不是有感而发,为情而作。而"以笺注入诗","以考据为诗","以学问为诗","误把抄书当作诗",便既失去主体灵性,也失去客体灵性,丧尽"天真",也就失去作诗的依凭,因而写出的诗便失去诗之审美本质,成为"伪诗",自然就会陷入"来先无谓去无端"(《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的境地,徒拾人牙慧,如鹦鹉学舌,所吐者非以自己口达自己心的"人言",而是"呓"(梦话),是"痁"(发高烧时的昏话、胡话)了。所以船山讥之为"饤饾古人书(《论诗十二绝句》)、"颟顸书数语"(《论诗十二绝句》)。袁枚在前,船山在后,中间还有喊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的赵翼,异口同声,反对以笺注、学问入诗和依傍古人,而专主性灵,提倡创新,提倡诗要表达真情实感。
最后还要指出两点:
一是张问陶与袁枚同属性灵一派,袁为主帅,赵翼为副将,张为殿军,袁入翰林比张早50年,张父与与袁在京时同为执友,那么他们的诗歌观点是否有师承关系?船山在《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中说:"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张、袁一生未曾谋面,以文字结交时间较晚,结交之前,张问陶已早高擎"性灵"大旗。仔细比较,二人观点确也略有不同之处。袁枚主张的"性灵"是:"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袁强调"著我",但更强调的是"灵犀",即"灵感"、"天才"的具备。张问陶提倡的"性灵"是:"天籁自鸣天趣是,好诗不过近人情",强调的是主体的性情、个性的张扬和客体"天趣"、"天真"的自在表现,比袁枚更务实,更具唯物主义精神。他们标举的性灵均源于《毛诗大序》"吟咏性情"的主张,源于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而李贽同公安三表旌旗不远,更直接受影响于清代乾隆年间反封建禁固保守思想潮流的汹涌恣肆。时代风气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而,使袁张二人殊同归是很自然的。
二是丰富的人生履历和社会实践,使张在诗歌创作上有别于袁枚之处。他在《题屠琴隖论诗图》之九中说:"敢云老马竟知途,看尽寻常大小巫"。青少年时代全家困居汉阳达八年之久,有时竟"恒数目不举火"。艰苦的生活炼就了张问陶的人生识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他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起,就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南船北马的飘泊生活。三度赴京求取功名,历经鄂、豫、冀、鲁、苏、皖、陕数省,足迹遍历大半个中国,数过长江三峡、剑门、栈道、秦岭各地,遍游沿途风景名胜,雄山巨川。这些不平凡的经历,记录在他的近千首旅游诗中。具有代表性的如《咏怀旧游十首》之九:"秦栈萦纡鸟路长,三年三度过陈仓。诗因虎豹驱除险,身为峰峦接应忙。雁响夜凄函谷雨,柳枝秋老灞桥霜。美人名士英雄墓,一概累累古道旁"。丰富的人生履历和社会实践,以及勤奋的诗歌创作,使诗人眼界宽阔,心胸广大,识见高远,诗学理论于是更加成熟。先后写出了《宝鸡师壁十八首》、《拾杨梯》、《采桑曲》、《丁已九月褒斜道中即事》、《乡愁五首》等具有很高历史价值而足以流传千古的名作。这些具有杜甫"诗史"性质的诗歌是张问陶诗歌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即在诗歌内容上由前期的才子型的豪放疏纵转为后期关切民瘼、反映现实和暴露黑暗。坎坷的人生和曲折的履历,使张问陶虽然在诗学思想上与袁枚接近,但是在诗歌创作上却独树一帜。而袁枚三十二岁即闲居随园,作富贵闲人,过优游闲适的生活,因而诗作中不少价值不高的作品。比较二人之诗,正如朱文治在《书船山纪年诗后》所说:"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耽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
注释:
⑴《船山诗草》中华书局,1986处出版。凡以下张问陶诗,均引自本书。
⑵《艺术论》第47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⑶《美学》第一卷第372-37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⑷《美学》第三卷第192页,商务印馆1979年版
作者简介:罗应涛(1942-),男,汉,四川筠连县人,宜宾学院教务处, 教授。 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

 罗氏家乘
罗氏家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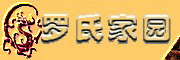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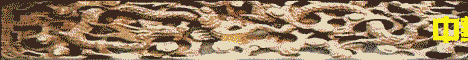
 罗氏家族
罗氏家族
 罗氏家话
罗氏家话
 罗氏家传
罗氏家传
 罗氏家书
罗氏家书
 科技天地
科技天地
 它山之石
它山之石
 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
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