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序:
跟随一个家族的足迹读历史
作者:罗 宏http://www.luos.org
本书写的是湖南鼓磉洲罗氏家族大约500年间出现的一些人物及其经历的一些历史事件。要是从族谱而论,我算是这个家族的第二十代传人,但这并不重要,几百年的演化,我与家族的关系只是中国民俗意义上的敬意,类似中华儿女对“炎黄子孙”一词形成的心理情结,书中聚焦的众多人物,我仅得见数人而已,此前更谈不上了解。我花了五年时间,查阅了包括族谱、族人遗著在内的数千部(篇)历史文献,达数千万字,寻访求教四方相关族人和专家数百人,鉴别取舍,消化思考,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这主要是因为家族的人物和事件令我非常痴迷而高度关注。
这个家族的一代代人物绵延地行进在由明代至民国500余年的历史途中,奇迹般地踏着历史的大部分节点,并且身体力行参与了历史塑造,比如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大潮,比如明末的湖湘抗清血杀,比如南明王朝的最后覆灭,比如岳麓书院的清代辉煌,比如经世派精英集团的形成,比如湘军的崛起,比如平定太平天国的鏖战,比如鸦片战争,比如洋务运动,比如抗法战争,比如西北平定和新疆收复,比如湖南宪政运动和留学运动,比如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难,甚至后来的五四运动、农民运动、秋收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这个家族的人物及姻亲友人们都在其间占有一席之地。我当然知道三湘四水有着更显赫的世家望族,但是这个家族持续显望500余年之久,其族人经历了这么多重大历史事件,是否也很普遍,见识不够的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我被这个家族与历史的复杂纠缠所震撼。这个家族为何能在湖湘大地持续显望500余年?其族人参与了那么多历史事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为什么那么踊跃地投入诸多历史漩涡中成为弄潮儿?其实在他们同时代更多的人选择了观潮,是什么力量吸引他们奋不顾身?他们如此这般的人生姿态,又给今人怎样的启悟?这些问题使我萌生了求索和书写的强烈冲动。
显然,仅凭查阅族谱,摘抄一些生卒年月、学历官职、若干政绩或著述,外加诸多名家点评,是难以解答这些问题的,还必须追随且超出这个家族的足迹,深入他们所参与的历史事件中,深入与他们发生纠葛的各种人物事迹中,才能真有收获。打个比方,我不能只关注家室之内的陈设写家室,还要推开窗棂,关注家室外的风景,才能写出富有意味的家室特色。比如,我发现窗外是一片热带雨林,便豁然明白为何家室内的陈设是具有热带雨林风情的设计。一句话,这是需要大视野的工程。
尽管已有学者论断,中国千年的社会结构是皇权与族权的结合体,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就是“家国结构”,家族是缩小的国家,国家是放大的家族。但是随着文明的推进,这种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变,当下,我们看到的是自上而下直到村寨的行政体制,此前行政体制止于县衙的局面荡然无存,人们雀跃于公民社会的诞生,家族成了一个消逝的记忆。其实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我们并没有深刻地体认到这种社会结构对中国文化与国民性带来的深入骨髓的影响。宗法家族曾经的历史存在,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方面全方位地决定着中国精神与面貌,时至今日,它深深的烙印还不时地浮现。我们的反思还失之肤浅。流连于家族的史料中,我非常感性而非概念性地体会到,如果能深入地剖析家族,尤其是作为家族高地存在的世家望族,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将大为深入。因此,把罗家作为一个标本来叙述并且剖析——无论正面还是负面,也许能推动我们进一步认知中国千年的家族现象,更理性地思考民族未来的生存。
鼓磉洲罗氏家族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崛起,家族中被方志以上史籍记载的名人有近百人之多,显望于湖湘500余年之久,财富、权力、文化以及联姻四大因素的结合是该家族持续显望的奥秘所在。罗家名人中富豪和高官并不突出,但文化名人,尤其是从事教育的文化名人社会影响力很大,比如罗典,作为岳麓书院的山长,以及两位萧规曹随的高足袁名曜和欧阳厚均,开创了清代岳麓书院最辉煌的时代,长达60余年,可以说,湖南近代史上半数以上的著名英杰都是罗门弟子,堪称奇迹。此奇迹弥补了罗家在权力和财富方面的不足,在英杰弟子们的推崇下,罗家赢得了湖湘社会的广泛尊敬。加上后来罗修源、罗汝怀、罗正钧、罗正纬、罗暟岚、罗正璧等族人持续在湖湘社会产生的文化影响,罗萱、罗逢元兄弟等一大批罗家湘军骁将的显赫军功,构成了这个家族文武双全的社会张力。罗家还与许多其他湖湘世家建立了密切的姻亲关系,如和著名的方上周氏家族长达300年的联姻史,以及和湘潭黎氏家族、王闿运家族,湘阴郭嵩焘家族,长沙张百熙家族、王先谦家族等的姻亲关系。还有和张治、钱沣、严如熤、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贺长龄、贺熙龄、何绍基、邓显鹤、陈宝箴、陈三立、赵启霖等的师生情和朋友情。这些都是罗家巩固家族势力的有力支撑。罗家保持了500余年持续不衰的望族名声,打破了显望“不过三代”的民间说法。这种家族现象除了有强大权力支撑的皇室显宦之族,在乡土中国实属少见,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族群案例,不可多得。而其中蕴含着的某种家族智慧,不仅惠及家族的发展,还丰富了我们的社会学认知——正面的和负面的。
罗家以文化立族,数百年历史中,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代代相传,可谓皇权制度的忠诚卫士,罗汝怀给曾国藩策划组建湘军的建言中,便主张以富家子弟为骨干,提出了国有难,富家子弟应身先赴死的思想。事实上罗家子弟也身体力行,咸同年间参加湘军的罗家子弟,估计占当时罗家适龄男丁的近半数。500多年来,但有国难,罗家子弟以身殉国,以家殉国,乃至以族殉国,遭到家族百口灭门之祸也义无反顾,这种对王朝的忠贞,是怎样融入了家族的血液中,难道不值得玩味吗?更有意味的是,到现代,又涌现了罗学瓒、罗哲这样的叛逆子弟,同样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跟随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成员,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最后英勇就义;同时,依然有罗家子弟继续坚守保守主义的罗家族风,于是就出现了新与旧,保守与激进的转型和复杂纠缠,而且在纠缠中,族情未断,这难道不也值得思考吗?
诸此种种,显然都不能仅仅理解为家族个性,还关涉时代个性以及时代与个人的复杂互动。这就使我更具有一种解剖的心态,从而构成了相应的写作姿态。
首先,我比较关注环境对这个家族的影响,因此往往会在时代背景和这个家族的社会关系方面投入相当篇幅。也许有人会觉得有些游离主题,有些虚焦,我却认为如果对环境有足够了解,对于该家族存在的理由会体会更深刻。况且,有些时候,这个家族的某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把我带进某个历史场景,让我发现了从其他视角难以看到的历史细节,这种情形下,某个族人的作用不过是个向导而已。坦率地说,我更感兴趣的是历史姿态,如果这个家族的这些人物不是镶嵌在历史中,我肯定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书写欲望。这一点,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宽容和接纳。
其次,我在书写中也面临所有书写历史的作者的困扰,即史料缺失导致的史实迷茫和断裂。于是我也像许多撰史者一样,根据遗存的史料,怀抱真诚,遵循逻辑,去分析推断当事人可能遭遇的生存境遇。我相信,史学书写离不开探秘和猜测,甚至可说排除探秘和猜测,往往就难以接近历史。在中国,大约从司马迁开始,在西方,则有荷马、希罗多德等,他们都是依据遗留的史学痕迹,进行认真考证、探秘、猜测,加上合理想象构建历史——史学研究和书写的魅力,很大程度也就在此。当然,这都是我对史学的认识,但凡推测,我必会给予申明。我不指望读者全都信赖我的研判,我当然也知道,还有一些不见材料不说话,材料说到哪话就说到哪的严谨学人,未必会认同我的方式,对此我只能期盼读者宽容我这个业余撰史者的不够严谨了。
再次,我在叙述中还夹杂了不少议论,这是我读史的感悟,我写这个家族的故事,最终目的就是收获某种感悟。即使不够精辟,也显示历史对后人的触动,因而历史就依然活着。也许这些感悟在智者面前会显得十分幼稚,不值一提,却是我的心声,我很难压抑也不想压抑。有文学经验的我也知道,这会影响叙述的流畅,影响到本书的可读性,但是我要是压抑自己的心声表达,又会失去写作的欲望。我的许多文学作品,也带着同样的痕迹。我非常推崇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我认为昆德拉的所有文学书写都是围绕哲思而展开。我受昆德拉的表达方式影响较深,形成了自己的写作个性。所以,我也想告知读者,希望得到理解和宽容。
最后,我在史料上下了不少功夫。希望用更多的史料,避免我过多的主观武断,也供有心的读者依据史料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我在行文中大量地引用了史料。可以说,关于罗氏家族的史料,本书的披露是目前最为丰富和全面的,这也是考虑到,对于有关湖湘地方文史研究,这些史料具有资料价值,我等于做了某个专题的史料整理,希望给同行提供一些方便。这当然又可能会影响文字的流畅,但是权衡之下,我还是保留了这些史料。
于是,一个可能会引起困惑的问题又出现了:我的这部书稿属于什么文体呢?它是史述专著吗?还是一部史论著述?或者是一部历史大随笔?一部历史报告文学?书稿完成后,我也一度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带着这个问题对比性地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发现,他在书稿出版时,也经历过类似的困惑,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不伦不类”,无论是经院的史学出版人还是商业的文学出版人都觉得不像他们熟悉的文体,以至于一度都不接受出版。后来黄仁宇的这部书还是出版了,并且风行至今。也就是说,自黄仁宇之后,有了一种新文体,不妨叫作“万历十五年”体。
我这么说,绝不是狂妄地将自己和黄仁宇并论,在他面前,我是班门弄斧。我只是想说一个感悟:文体是为表达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从发生学而论,一定是先有自由的表达,并且自由的表达积累到了相当程度,才出现文体的总结和规范。所以,符合心愿的表达是第一位的,文体只有在成全表达的意义上才具有合理性。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例,从书名而论,它讲述的似乎应该局限于万历十五年(1587),可是该书所涉远远超越了这一年,在黄仁宇笔下,万历十五年的事既不占主要篇幅也不重要;在表达方式上,文学手段和史学手段交织,考证、引证、注解、叙述、议论、分析、推理、猜测等都用上了,为此我还做了笔记。于是我释然了,自己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达不到黄仁宇的精彩,也不算太标新立异。我说这些,无非还是希望读者对我的个性表达多一份宽容,多一份耐心,我真心想把我的所见、所叙、所感与读者分享交流,但又担心种种难以压抑的个性表达影响了我与读者的沟通,故此表白。
我还明白,任何历史都无法还原到其自在的本相,所有的历史都是撰史人眼中的历史,撰史人的修养和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叙述的模样。此外撰史人还受制于史料——史料缺失是普遍的现实,且不说史料本身也有欺骗性,引用时也要小心翼翼。所以历史写作,也是对残缺史料的一种补白和校正。比如说,罗家许多应该极有故事的人物,都面临这种尴尬,对此我只能尽力搜寻史料并小心求证,还不能保证穷尽了相关史料。所以只敢说,本书对鼓磉洲罗氏家族的整体史料搜罗是最全的,但不敢说没有遗漏。因而我的书写和他人的书写出现差异,也并不奇怪,我也无意辩解何种书写更为真实。亚里士多德说过,真实只是意味着相信而已,我根据掌握的史料,相信自己的观察,书写中没有刻意欺骗,这就是我的真实承诺。当然,这种真实承诺依然有主观片面性。比如,我笔下呈现出来的这个群体风貌基本上是正面的,据常识经验,这肯定是片面的,罗家肯定有不肖子孙,肯定有阴暗的故事,但这些不肖子孙或者阴暗的故事,在本书中基本销声匿迹。这是因为我没有发现这样的史料——如果发现,且觉得有启迪价值,当不会回避。所以,我只能在书写中贯彻“病理研究”的初心,就我掌握的资料展开剖析,对于他们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我自认为还是有相当的批判性的。还记得维特根斯坦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如果我说的和他人说的雷同或者不同,高明或是肤浅,都意味着我只是说出了我看到和能说出的一切,仅此而已。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师友亲人,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该感恩的这个阵容达数百人之多,恕难以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但他们给予的帮助我会铭刻在心。谢谢了。
|
 罗氏留言
罗氏留言  罗氏论坛
罗氏论坛  罗氏家乘
罗氏家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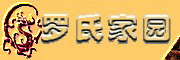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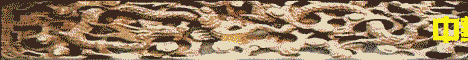
 罗氏家族
罗氏家族  罗氏家话
罗氏家话  罗氏传承
罗氏传承  罗氏文苑
罗氏文苑  科技天地
科技天地  它山之石
它山之石